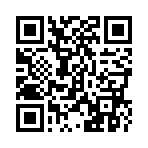2005年09月23日
POJ很難看懂嗎?
最近常有朋友提及:POJ等拼音文字,因"感覺不好阅读”,而主张等闲處之。為此,在下就便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,如下(因考虑到可能有闽南语區以外的朋友來訪,經思考再三,本篇决定以華文书寫。這也是小站迄今第二篇華文作品哦~~)。
个人的“意識型态”比较容易在有意或無意之间主导了人的意向和动向。比如我也常犯此错误(尽管我至今不过是一碌碌無为的無名小卒罢了!)。
个人的“意識型态”比较容易在有意或無意之间主导了人的意向和动向。比如我也常犯此错误(尽管我至今不过是一碌碌無为的無名小卒罢了!)。
从国家的高度看(有点搞笑,居然谈到这么高的层次~~XD):我国政府居于国家统一(包括文化整合,意識歸一)、人民和睦的原则,认为大家(僅表示漢族)最好都讲北京话(實際上是“要求”,更近乎强迫),最好少说“方言”(中国人对该词的理解似乎普遍存在偏差),当然不说更好。文字方面,唯尊汉字,在这样的国情下,本也无可厚非。如此一來,那些平日只能躲在黑暗角落里苟延残喘的羅马字,就会相当自然就走上了“非法的道路”,自动成为过街老鼠也實在不算稀奇。闽南有一句俗语,曰“狗死,狗虱也著無命”,且看,现在几乎所有的母语方言都差不多快修練成高级社会里人見人恨的“滅絕師太”了,再看那些付诸于母语方言身上的羅马字则更顯碍眼,不除之後快才怪呢!
再來看一看那些语言学家、方家的态度吧。勿庸置疑,我国的学者,其学术学平都是相当高的,搞学术研究的态度也绝对称得上一流。他们大多很忠實,很勤恳,所以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一向值得称道。但也恰恰由于他们一向的忠實,忠實于一些可能不见得合理(但合法)的政策,所以他们也和政策本身越來越相像,时间久了,就和“政策们”混然一体了,“政学”不分了。所以,学家们自然都是反对(应该说看不起或者不当一回事比较贴切)他们眼中“不入流”的羅马字。
這样,失去以上两个“高层”支援的羅马字们,差不多也是垂死的。
百姓呢。人们常说,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是的,或许有些东西确實需要时间來证明和考验,过早下定论或有断章取义之嫌。话说回來,有些东西,你或许根本就没見过、來不及見,好一点的话,可能还道听途说过。这样的东西,对群众來说,不可谓不少。造成“看不見、听不到”很多时候其實不是群众願意,群众更多时候只是受众的角色,而無取绝权。以前的闽南POJ,绝绝对对是在闽台地区起着一定的文字功能,帮助不少汉字文盲得以接受高阶文化。当然,后來由于社会变迁,国策使然,这些东西也不复存在了(仅仅表示:在大陆不存在了)。它们的命运似乎就是今后诸多汉语方言的命运。所以,有些东西,很难定谁是谁非,只能说谁强谁弱。勝者为王,但不一定只有王者才拥有真理。
现在,似乎只要和台湾有关的东西,多多少少都会被贴上一层与政治有关的不良标签。如前所述,POJ产生于早前的闽台社会,长于此,也曾用于此。后來,漢字至上論起來了,这样的拉丁文从起初被逐、到最终没落,确也不难理解。不过,POJ在台并未消失得如闽南那么地徹底,相反,虽也曾一直被狗日本和KMT通缉,但却坚强地挺了一百多年,直到現在。且不管POJ是洋教士來发明,總之它至今还在台湾的一部分民众的生活中(不光是教会,据说教会之外的人士更多)。他们用POJ,歴來有传统,很习惯,道理就像很多用漢字的人一样。所以,他们怎么会存在“不好阅读、瞧了头痛”呢?其實,这只是一个习惯问题。一种事物,对于没接触过、或少接触过的人而言,它肯定是陌生和生疏的。这好比,语言学家的口语水平可能比一个不识字的农民还差几倍,这是有可能的。但是,语言学家不能以自已的个人标准去下定论,把那个农民的口语否定得一文不值。同样地,语言学家看不懂POJ(或说看不习惯),可能是因为他们本身没机會或很少接触(如前所述,羅马字在漢字圈似乎是洪水猛兽),或者他们因为不屑接触,所以他们自然很生疏;而相反地,经常使用的人,哪怕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,也会比那些语言学家们熟練得多。所以,這不是对与错,该与不該的问題,而是刚刚说到的“习惯问題”(不谈文字本身的严密性、完美程度)。
至于谈到“口音差”。这个更不是一个问题,像POJ这样的拼音文字,本身就是辨音功能的,这正好是它的一大特点。其實它的最大缺点才是不具备漢字所具备的辨义功能(这又是另外一个方面的话题了,不是本篇讨论的对象)。實际上,以往在纯泉腔或纯漳腔的地方(比如,漳浦和惠安、泉州一带),都有使用POJ的情况(是一定群体内使用,非个例)。这些纯泉腔或纯漳腔地区,为何能够使用POJ(POJ最初是据厦门腔制定)而無障碍呢。我想那是因为该地区使用者已經在潜意识里将POJ的符号当成一种文字,而非纯綷当成拼音。當有一個完整的POJ单词(字)擺在那裡,不同地区(實际口音有所不同)的人看到了,就会读出不同的腔调。比如说,POJ的"ke-têng"(注:家庭)一词,漳州人看到了,就會读成/kɛ⁴⁴/ /tiŋ¹³/;而厦门人则讀为/ke⁴⁴/ /tiŋ²⁴/。再比如,POJ的“hé-hu” (注:火灰)一词,厦门人會讀为/he⁵³/ /hu⁴⁴/;而泉州人则讀为/hə⁴⁴/ /hu³³/。如此,它其實也有兼备一定的辨义功能(当然这一点遠不如漢字)。关于POJ如何應對不同口音的規则,在下也曾于《闽南白话字语音系统》一文中有所说明。
再來看一看那些语言学家、方家的态度吧。勿庸置疑,我国的学者,其学术学平都是相当高的,搞学术研究的态度也绝对称得上一流。他们大多很忠實,很勤恳,所以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一向值得称道。但也恰恰由于他们一向的忠實,忠實于一些可能不见得合理(但合法)的政策,所以他们也和政策本身越來越相像,时间久了,就和“政策们”混然一体了,“政学”不分了。所以,学家们自然都是反对(应该说看不起或者不当一回事比较贴切)他们眼中“不入流”的羅马字。
這样,失去以上两个“高层”支援的羅马字们,差不多也是垂死的。
百姓呢。人们常说,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是的,或许有些东西确實需要时间來证明和考验,过早下定论或有断章取义之嫌。话说回來,有些东西,你或许根本就没見过、來不及見,好一点的话,可能还道听途说过。这样的东西,对群众來说,不可谓不少。造成“看不見、听不到”很多时候其實不是群众願意,群众更多时候只是受众的角色,而無取绝权。以前的闽南POJ,绝绝对对是在闽台地区起着一定的文字功能,帮助不少汉字文盲得以接受高阶文化。当然,后來由于社会变迁,国策使然,这些东西也不复存在了(仅仅表示:在大陆不存在了)。它们的命运似乎就是今后诸多汉语方言的命运。所以,有些东西,很难定谁是谁非,只能说谁强谁弱。勝者为王,但不一定只有王者才拥有真理。
现在,似乎只要和台湾有关的东西,多多少少都会被贴上一层与政治有关的不良标签。如前所述,POJ产生于早前的闽台社会,长于此,也曾用于此。后來,漢字至上論起來了,这样的拉丁文从起初被逐、到最终没落,确也不难理解。不过,POJ在台并未消失得如闽南那么地徹底,相反,虽也曾一直被狗日本和KMT通缉,但却坚强地挺了一百多年,直到現在。且不管POJ是洋教士來发明,總之它至今还在台湾的一部分民众的生活中(不光是教会,据说教会之外的人士更多)。他们用POJ,歴來有传统,很习惯,道理就像很多用漢字的人一样。所以,他们怎么会存在“不好阅读、瞧了头痛”呢?其實,这只是一个习惯问题。一种事物,对于没接触过、或少接触过的人而言,它肯定是陌生和生疏的。这好比,语言学家的口语水平可能比一个不识字的农民还差几倍,这是有可能的。但是,语言学家不能以自已的个人标准去下定论,把那个农民的口语否定得一文不值。同样地,语言学家看不懂POJ(或说看不习惯),可能是因为他们本身没机會或很少接触(如前所述,羅马字在漢字圈似乎是洪水猛兽),或者他们因为不屑接触,所以他们自然很生疏;而相反地,经常使用的人,哪怕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,也会比那些语言学家们熟練得多。所以,這不是对与错,该与不該的问題,而是刚刚说到的“习惯问題”(不谈文字本身的严密性、完美程度)。
至于谈到“口音差”。这个更不是一个问题,像POJ这样的拼音文字,本身就是辨音功能的,这正好是它的一大特点。其實它的最大缺点才是不具备漢字所具备的辨义功能(这又是另外一个方面的话题了,不是本篇讨论的对象)。實际上,以往在纯泉腔或纯漳腔的地方(比如,漳浦和惠安、泉州一带),都有使用POJ的情况(是一定群体内使用,非个例)。这些纯泉腔或纯漳腔地区,为何能够使用POJ(POJ最初是据厦门腔制定)而無障碍呢。我想那是因为该地区使用者已經在潜意识里将POJ的符号当成一种文字,而非纯綷当成拼音。當有一個完整的POJ单词(字)擺在那裡,不同地区(實际口音有所不同)的人看到了,就会读出不同的腔调。比如说,POJ的"ke-têng"(注:家庭)一词,漳州人看到了,就會读成/kɛ⁴⁴/ /tiŋ¹³/;而厦门人则讀为/ke⁴⁴/ /tiŋ²⁴/。再比如,POJ的“hé-hu” (注:火灰)一词,厦门人會讀为/he⁵³/ /hu⁴⁴/;而泉州人则讀为/hə⁴⁴/ /hu³³/。如此,它其實也有兼备一定的辨义功能(当然这一点遠不如漢字)。关于POJ如何應對不同口音的規则,在下也曾于《闽南白话字语音系统》一文中有所说明。
Posted by limkianhui at 22:00
│華文地帶